观影指南
无需安装任何插件,日本电影《鸢》正片即可免费播放。
DVD:普通清晰BD:高清无水印HD:高清TS:抢先非清晰
如果电影《鸢》加载失败,可刷新或切换线路
未来影院为您提供电影《鸢》正片免费播放地址,如果电影《鸢》播放失败清按F5刷新再试,或者切换播放资源,请勿轻信《鸢》视频内广告,本站与广告内容无关.
请收未来影院唯一网址 [ http://www.qfanyi.com/details/18643.html ] 以免丢失!
《鸢》剧情:重松清的小说《鸢》将首次被改编成电影,小说曾经获得“大家所选选角川文库感动第1位”影片将由濑濑敬久([天堂的故事])执导,阿部宽和北村匠海([念念手纪])在影片中扮演父子,故事讲述了在80年代的日本,市川安男是一个在货运公司工作的职员,他的妻子市川美佐子刚刚产下他们的儿子旭,然而一场意外,让美佐子失去了性命。安男与身边的人们为了保护旭,他们决定不告诉旭他母亲的这场意外,影片将于2022年日本公映。
为您推荐
用户评论
-

Jensen
这部电影总体上不如预期得那么好,我感到有些失望。
单调的剧情和慢节奏让两个多小时显得冗长而乏味,电影演到后半段,我直接1.25倍速和2倍速之间来回切换。
不过父亲为了让儿子没有负担地、健康自由地成长,将妻子真正的死因(妻子为避免儿子被箱子砸到,用自己的生命挡了下来)长久地隐瞒下来,这点确实值得肯定。
看到这里的时候,我就想起了中国父母对孩子从小的道德绑架和日常pua。
我想中国父母会用这样的话术:你妈为了救你把命都搭进去了,你还不好好珍惜现在,不好好学习?你这样对得起你妈吗?
如果一个孩子,从小到大都被这样的话围绕左右,相信他的心态一定很糟,他每天都要带着负罪感活下去,这简直生不如死。
不过还好,小旭有一个好父亲,庇佑了他成年之前的那段人生。
PS:滨田岳真的好小一只啊,在阿部宽面前显得更小了吧,附图一张。
 看看这身高,哈哈哈哈
看看这身高,哈哈哈哈
-

Jensen
这是一个关于父子的故事。市川安男是一个搬货的工人,粗糙脾气暴躁,有干劲爱喝酒。但他有一个贴心的妻子并即将拥有一个儿子。安男夫妻都没有父母,所以他们也在学习如何成为父母,但在儿子年幼的时候,为了保护他,妻子离开了人世。儿子逐渐长大,在朋友的帮助下安男陪伴了儿子的成长,看着儿子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,直至生命的结束。
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,之前拍过剧,这是第一次拍电影。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感人,单身的父亲和儿子一同成长,时间跨度大,人物的情感丰富。但更打动我的是来自其他人的善意和支撑,不管是老和尚一家将孩子视如己出的照顾,还是对孩子的教育,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看到长大后的儿子将手放在妻子和前夫的儿子背后时,我想他心里一定有老和尚在海边对他说的话。另外还有工友的关心,饭店老板娘的关爱等等…就想叔叔说的,他是大家的孩子呀。
因为希望孩子不要心怀愧疚的长大,所以独自承担了妻子去世的谎言,作为父亲,安男是称职的。只是父爱大多沉默又不好表达,偶尔会伴随一些冲突和暴力,这也是安男在成长中和儿子共同面对的课题。但也如他期待的,他有一个像妻子一样的贴心的儿子。
看电影的途中数次热泪盈眶,真是的感情往往是最打动人的。日本电影总是在人与人的情感方面表现的特别温柔,一些细小的光影和眼神的描绘总让人特别容易共情。父亲的坚强,邻里的关爱,和自己的家庭的关爱,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不断传递,继承,延续。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,贯穿爱与学习。
-

Jensen
2/3是在飞机上看的默片,但似乎不影响理解和入戏。底层平凡但幸福的三口之家,父勤母善,本来可以一起带着孩子奔向更好的未来吧 母却因救儿永远退出了这个“完美组合”, 留下了时暴时躁、无限自责的父亲和记忆模糊却思念母亲的儿子。片子以母为名,讲述的却是父子相伴相爱与相杀。
喜欢这个不完美父亲,虽然情绪不稳,会酗酒消愁,会简单粗暴,但始终没忘要带着和妻子的共愿:让儿子健康成长成人。所以他会把妻子之死甩锅到自己身上,自残式教育儿子远离暴力,在不舍的纠缠中放手儿子东京奔前程,愤怒中挣扎里接受儿子的感情选择……似乎每个行为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,但甘之如饴。
儿子是不幸也是幸运的,幸的不止是有用心良苦的父亲,还有很多大家长们的关心,大人们用各种方式关心呵护着他们“共同的儿子”,他们的温暖赋予这个家庭特有的完整感。
Ending 很治愈,两个不同程度的“破碎”家庭重组融合,海边其乐融融,大写的“幸福再出发”
-

Jensen

最近连续看了两部亲情主题的电影。一部中国的《妈妈》,一部日本的《鸢》。
《妈妈》讲述85岁母亲和65岁女儿的感人故事,女儿终身未婚,热心公益,但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,记忆在不断流失,性情起伏不定,本来一直被照顾的老母亲又重新做起了“妈妈”,照顾女儿,抚慰女儿。
《妈妈》的优缺点都很突出。两位老戏骨吴彦姝和奚美娟的表演极为精彩,阿尔兹海默症患者、女性群像和老年生活也是国产大银幕上极为稀缺的意象,电影用非常温情的视角投向这些生活中不被注意的“边缘人”,除了患病后的恐惧和艰难,意外离世的父亲作为不可言说的隐线贯穿全片,既是女儿个人的心结与父爱缺失的遗憾,亦是大历史洪流下被湮灭的个体的无力,“母爱”作为融化一切冰霜雨雪的力量包裹所有人物,消解所有不安。八十多岁的妈妈为了照顾女儿,开始锻炼身体,学习生活技巧,忍受女儿的言语甚至暴力攻击,本身已经具备打动所有人的能量。电影再次展现甚至强化了“妈妈”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牺牲一切、忍辱负重、为母则刚的形象,影片中甚至重新唱起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唤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的催泪记忆,洞穿了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多年当代史。历史在发展,物质在进步,但我们的精神内核并没大的改变。
电影的最大亮点是表演,但除此之外有太多遗憾。电影整体太个人化,母女优渥的生活环境、封闭的人际关系、过多抒情化浪漫化的镜头,让电影的故事不接地气,难有代入感,通篇只是让人看到“悬浮”的母女情深,“不良少女”的段落更是突兀和理想化,电影也许想涉及的某些议题浅尝辄止、一笔带过,失去了对更广阔的社会与现实的观照,电影就变成了一篇自说自话的伤感文章。“母爱”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滤镜和光环。
同样类型的家庭题材电影《鸢》,讲述的是父子情。阿部宽饰演的父亲幼年丧母,父亲离家出走,他被亲友养大,认识了同样失去父母的妻子,生下儿子小旭。一次意外中妻子为了救儿子去世,儿子年幼始终不理解母亲的离世,父亲为了不给儿子留下阴影坚持隐瞒真相,含辛茹苦把小旭养大,直到他上大学,成家立业。
阿部宽非常适合粗犷刚硬、倔强善良的父亲形象,家庭题材作为日本电影的常规类型之一,贡献了很多经典角色和演员,比如老一代的高仓健,常青树役所广司。《鸢》里的父亲也非常符合东方传统文化里的典型形象。他大嗓门,能吃苦,爱喝酒,爱打架,对妻子温柔深情,对儿子呵护备至。妻子的早逝让他对儿子多了愧疚,既当爹又当妈,希望靠自己的全心付出能让儿子健康成长有出息。
从儿子的角度,他一直觉得母亲的去世有问题,却总得不到正面的回应,成为他的心结。大老粗父亲不懂沟通,不爱表达,有事都藏在心里,无形中也制造了隔膜,儿子能感受到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微妙又尴尬。
电影里的父亲是典型的严父,主张严厉管教和保姆式照料,电影中两次大的父子冲突都来自这两点。
第一次是父亲因不满意儿子在棒球队体罚学弟,儿子顶嘴,父亲一拳打在脸上。事后父亲虽嘴硬心里也别扭,但依然要求儿子要跟老子道歉,儿子争不过便跑,父亲跟出去,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,自己把自己一顿暴揍,自责没有把儿子教育好。
第二次是儿子考上早稻田大学,要去东京读书,父亲不放心坚持要一起去,儿子不愿意,父亲伤心饮酒,借着酒劲对儿子又是一通教育,儿子回嘴,父亲更生气:“想想你是谁带大的,现在有什么资格教训我,快道歉。”
对于“父亲”,管教孩子,是义务,也是权力,不需要回报,但也不能拒绝。
儿子虽然在父亲面前乖巧,但成长在新环境下的一代已然不认同上一代的观念,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一步步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空间,软弱但坚决。
父亲最终同意不去东京,两人闹得很僵,告别时像诀别,父亲说:“听好,是你自己要去东京的,到时候别跑回来诉苦,你要死在路边都行,我是不会去东京了,我去东京时就是帮你收尸了,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,我是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。”用骂人表达关爱,用诅咒展示担忧,这样的父亲可恨又可爱。儿子走后留下一封信,为他的衣食住行做了很多安排和叮嘱,父亲终于按捺不住,追奔而去,对着儿子的身影大喊:“你要加油!”
父亲崇尚的是传统社会的男性形象,强壮体魄,养家糊口,自尊自强,他满意自己的搬运工工作,会骄傲的对儿子说“这样的工作才有男子气概”。他把自己后半生目标全都放在儿子身上,一方面自己很累,无怨无悔,一方面付出的越多,期待的越多,他期待儿子生活越来越好,但又不清楚什么是好。时代变化太快,他已经无力把握。儿子的成长和独立,其实也是父亲的一次再成长和再独立,他要学会把儿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,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尝试去变化,懂得放手比懂得坚守更难。
父子的大和解是因为儿子的婚事。儿子在工作单位认识了女友,比他大七岁,离异,带一个三岁的孩子。父亲听了直皱眉头,没有反对,也没有同意。一年后再见,女友已经怀孕,朋友上演了激将法,大力反对婚事,父亲反而说出了心里话,维护儿子的选择。
父子和解不需要谁道歉,谁向谁低头,不语亦是交流。
电影后半段,父亲见到了临终时刻的自己的父亲,知道了他也一直惦念着自己,满怀愧疚。父亲原谅了自己的父亲。儿子通过亲友的一封信知道了母亲去世的真相和父亲隐瞒的苦衷,也终于释怀。
结尾处,父亲和儿子合力扛神轿,弥补了幼时的遗憾,也代表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传承。
和解,也许是所有亲子关系的终点,血缘是割不断的联系。
《鸢》的父子,幸运又不幸,他们和解了,但是用了将近三十年。这样的故事依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,依然在发生,怎样平衡家庭的和谐和个体的独立任重道远。
《鸢》的故事并无新意,表演和剧本也都中规中矩,属于日本映画的正常水准之作。和《妈妈》一样,伟大的母爱和父爱总能引起强烈共鸣,永远有魅力,也永远有讨论的空间。
以爱之名可以消除边界,这是东方文化的最大特色。来自母亲/父亲/长辈/前辈/上级/权威的爱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空间/心理/权责边界,用无条件的“爱”要求无条件的“悦纳和服从”,这是代际之间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,存续至今也很难用谁对谁错、谁进步谁落后来简单评判。“以爱之名”在危难时刻,会是一剂良药,雪中送炭,日常生活中,也许多是互相捆绑,彼此桎梏,疲惫窒息。
年轻世代想要获得支持和解放,首先要有耐心和尊敬,之后只能寄希望于长辈的内心纯良和忍痛割爱,就像电影《鸢》的父子。三代人的和解都用了数十年,代价不可谓不大,结果的偶然性也不能忽视。
电影里的大和尚劝慰阿部宽时曾说:“变成一片大海吧。悲伤就像雪,降落到地面,会越积越多,不过若是大海,不论下再多的雪,都会默默吞下。”
东方式的困境需要东方式的智慧。鸢的自由飞翔,需要大海的宽阔胸膛。父、母、子、女都是一只鸢,也都需要自己的海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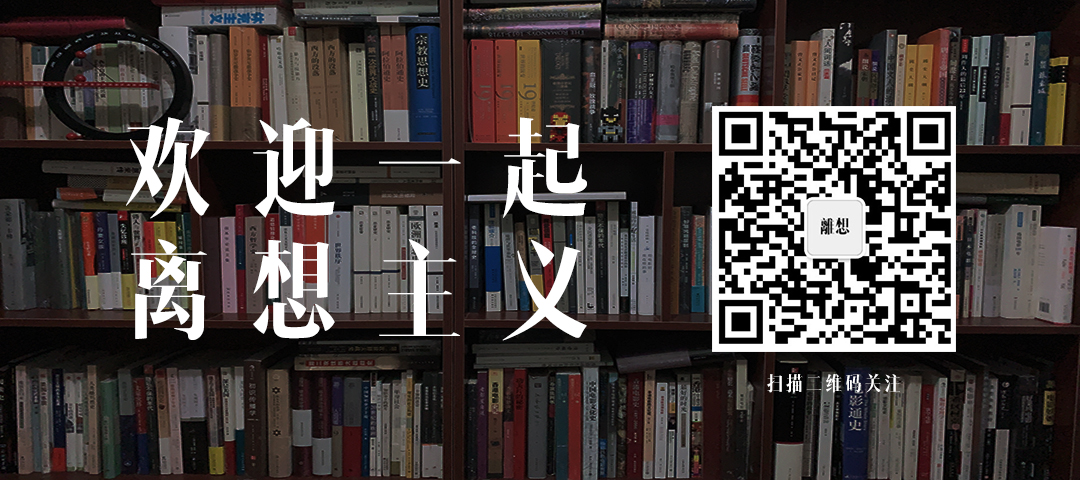
-

Jensen
原载《北京青年报》

文/淹然
■父爱文学与战后神话
重松清的小说《鸢》,是典型的东亚父爱文学。一边是不擅沟通的父亲,一边是倔强叛逆的儿子,最后互相理解,深藏的父爱得以揭露。濑濑敬久执导的同名电影(2022),是该小说的第三次影视化。看似俗套的戏码何以备受青睐?对此,一个简单粗暴的解释是,这种父子间无法正常表达爱意的故事,依然在现实里反复上演,《鸢》以温暖的细节和结局,治愈了那些受困于亲情隔阂的观众。
这个温情的父子故事,有一个惨烈的开篇——母亲的意外身亡。葬礼上,懵然无知的男孩,问父亲,妈妈怎么没来?众人动容,父亲紧紧抱住儿子。如何向儿子描述母亲的死亡故事,由此成为悬置于父子间的一枚炸弹。
唯一一次挑明,发生在一个浴室场景中。父亲与儿子裸露着身体,似乎预示着坦诚相见的可能。父亲一次次将头埋进水池,掩饰情绪的波动与泪水。他使劲揉搓头发,洗发水泡沫如厚厚的积雪,然而这个洗濯的动作并不意味着对真相的擦亮,而是一种反向象征——父亲最终决定将自己伪装成“历史的罪人”,将母亲救子的事实,涂改为妻子为救自己而死的善意谎言。
这个谎言持续到儿子成年才被戳破,但仍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形式,维持着父子间厚如墙又薄如翼的隔阂。在参加完成年礼后的某天,儿子接到了老和尚的来信,终于知道了母亲死亡的真相。而父亲那边,要直到儿子参加工作后,他才意外从儿子的作文《父亲的谎言》中获知,其实谎言早已崩解,儿子却什么也没说。
当儿子带着未婚妻突然宣告结婚的计划,父亲依旧沉住气,哪怕儿子正在陈说的内容会让多数家长惊讶——眼前的这个女子比自己长七岁,结过一次婚,还有个三岁的儿子。这里的视听表述极有趣,父亲只是干瞪眼,但背景中父亲的同事形成鲜明反差,偷听到这一爆炸性新闻的他,忽而端碗站起,忽而震惊得喷饭,犹如父亲隐秘内心剧场的显影。
影片将这份深沉父爱,冠以大海的意象予以总结。那是父亲最低落的时刻,他罕见地自我贬低:“我没生下来就好了”,那就不会出现妻子死亡、儿子丧母的悲剧。老和尚将他拉去海边,奏起全片的抒情高音:“悲伤像雪,落在地面越积越多,大海却可吞下悲伤,你要成为大海,别让悲伤落到孩子身上。”父爱如海,比海深,比海阔。海的意象不断出现,母亲在世时,三人一起在海边玩耍。儿子成家后,父亲在海边对儿子说:“当你痛苦时,只要想到最后还有家可回,就能继续拼搏下去了。”远处海天一色,几十年前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情境,如蜃楼般重现。
这个故事就这样从昭和37年(1962)一路讲到令和元年(2019)。六〇年代正是日本战后奋力重建之际,父亲生活工作的备后地区,按小说的描述,在战后凭借发展工业迅速繁荣,没有任何游览胜地,到处是鳞次栉比的煤气储罐厂和工厂。父亲的故事与时代的神话遥相呼应,而当故事来到衰落的令和时代,也正是父亲谢世、故事谢幕的时候。影片开头用两个镜头干净利落地交代了这种象征。一开始,是夜色中疲惫的父亲,车内广播放送着天皇病重的消息,这是昭和的尾声,泡沫经济的盛景即将燃尽。镜头一转,年轻的父亲活力满满,战后的复兴神话正热烈上演。
■男性气概与父之暗影
高大的背影,深邃的眼神,饰演父亲的阿部宽,让人想起高仓健。正巧,《幸福的黄手绢》与《远山的呼唤》这两部高仓健名作,翻拍时找的主演就是阿部宽。《鸢》里的父亲,像是两个时代的高仓健的综合体。
一个是山田洋次镜头里的后期高仓健,深沉如山。一个是黑帮片里的早期高仓健,如无脚之鸟,《鸢》里的父亲,在孩子出生前,酗酒又赌博。
影片反复强调着这种传统的男性气概。父亲将搬货时的工作场景比喻为战场,白色背心将古铜色肌肉衬托得格外耀眼,宛如古希腊雕像。当年,小林旭漂泊浪子的形象风靡一时,父亲最爱哼唱的歌曲就是小林旭的《炸药150吨》,因此,他给儿子取名“旭”。
但在这种雄性荷尔蒙的背后,潜伏着某种危险。和小说不同的是,影片以儿子的回忆口吻展开整个故事,这种追溯往昔的感伤氛围,让父亲的某些致命缺点与男性叙事本身的暗影,不至于过分刺眼。
父亲会在妻子挺着大肚子烹饪时,忍不住跑去酒馆。而他身上的暴力因子会不受控的暴发,在酒馆一言不合就跟老板大打出手,甚至在产房门前也按捺不住,向同事挥起拳头,在妻子辛苦生产的重要时刻,和人大吵大闹。
在父亲的世界里,暴力是必要的,也是男子气的应有表现。他对儿子和同学打架抱以肯定的态度,因为目的是正当的——儿子因丧母而受到嘲弄。当他教育儿子不该以暴力“教育”棒球社团的学弟时,他同样以暴力“教育”儿子,之后,他再次以暴力的方式自残,祈求儿子的原谅。
如此硬邦邦的传统家教,并非行之有效,父子关系因此不断爆发危机。但之所以每次都能过关,多亏小共同体的外部支援。换言之,父子关系的维持,很多时候要倚靠机械降神。虽然父亲生活的地方,鲜有美景,但商店街上的邻里熟人构成了紧密而温情的小共同体,酒馆老板娘,工厂的同事,在寺庙长大的发小,一个个胜似亲人。就像电影里反复响起的台词:“阿旭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啊!”
当父亲舍不得儿子去东京念书,大闹别扭时,儿子可以跑去父亲发小的家里“避难”。当儿子的婚事得不到父亲支持,是父亲的发小以激将法逼出了父亲的心里话,让这门婚事获得祝福。
身为早稻田大学高材生,最终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儿子,看似与工人出身的父亲是两种人,但其实,他不知不觉承袭了父亲的暗影。他同样缺乏沟通的耐心与技巧。他带着未婚妻跑回老家时,更多地是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,无论同意与否,这个婚都结定了。由此来看片中那个高光场面——当年儿子因病错过了抬神轿仪式,多年后,他终于和父亲一起完成了这个仪式——一方面,这意味着双方的终极和解,一方面也意味着,这对父子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,长大的少年终于变得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父亲一样,兼具温柔与固执。就像阿旭当年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玩具火车,而现在,阿旭送给儿子的也是一部玩具火车。
《鸢》是一部十足的男人戏。主角父子是绝对的核心,男性长辈的相继离世,催促着男性后代的成长,而骨肉匀停的女性是缺席的。母亲早逝,儿子的未婚妻宛如职业女性的简笔肖像,父亲发小的妻子近似小旭的干妈,也只是戏份可怜的功能性角色。不过,正是几个有限的女性角色登场的段落,松动了密不透风的男性叙事。
在父亲激动畅想儿子将会成为艺术家时,妻子语气平和,说起自己小时候读书就不太好,儿子多半会像自己,是个平凡的男孩。
另一处,是酒馆老板娘的隐秘前史揭晓的时候。原来,她有个女儿。因为农村重男轻女之风,女儿的出生引来周遭轻视,于是她抛弃女儿,只身闯荡异乡创业打拼。而在女儿即将成家,与母亲重逢之际,酒馆老板娘只是以一碗蛤蜊汤,祝福新人,最终也未参加女儿婚礼。尽管这条支线仍属于对亲情主题的一次呼应与强调,但罕见地,女性没有被习惯性地摁进伟大母性的框架中,出于个人意志与欲望的逃离得到了肯定。
最后回到片名“鸢”。鸢指的是片中的父亲,用原著的话解释就是,麻雀居然可以抚养出老鹰。片尾,阿旭的房间里贴满自己荣获文学大奖的剪报,这正是雄鹰高飞的象征,但阿旭却回答不出,父亲这一生是否幸福,恐怕阿旭也说不清自己是否幸福。毕竟,雄鹰是不被允许表达软弱的,亦如片中的父亲是不能轻易落泪的。